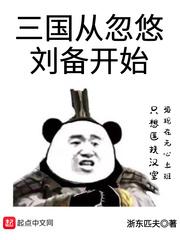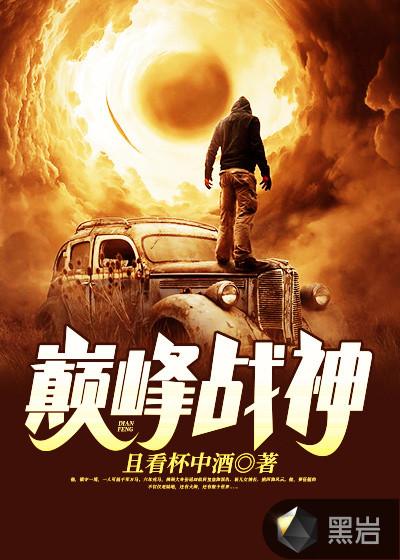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297章 廷杖(第1页)
年丞运立马拱手道:“请皇上明察!臣与太子有书信往来,完全是因为修筑城墙,困难重重,问题诸多,若每次都派人传话,花费时间太多。且信中所谈全是营造城墙之事,并非谋逆!”
字字句句,铿锵有力,慷慨激昂。
有几个中立派立马跟上,帮年丞运说话。
皇帝更生气了,“朕看你往日还算安分守己,克己奉公,所以才派你与太子共事,不曾想你也做出了结党营私一事!实在太令朕失望了!”
这番话实在太令年丞运寒心了。
他这么多年,兢兢业业,在储君之位的风云诡谲中逆风而行,虽艰难,但也做到了独善其身,坚定自己的立场,无论威逼还是利诱,他都不曾动摇。
可皇帝却凭几封再正常不过的来往书信,就认定他结党营私,甚至扣上个“谋逆”的罪名。
实在令人寒心!
不仅令他寒心,也令许多忠心耿耿的中立派寒心!
年丞运是中立派的核心,他德高望重尚且如此,何况其他人,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他们其中一个。
中立派的人,面色如土,心悬到了嗓子眼。当然,太子党和庆王党的人也好不到哪去。
一时之间,文武百官不寒而栗,纷纷夹起尾巴。
秦君郁辩驳道:“父皇,儿臣与年丞相一起负责城墙营造,有书信往来皆是为了方便公干,且信中内容除了公务,并未涉及其他,何来谋逆一说!”他语气冰冷,态度强硬。
就是怕有这么一天,他用词小心谨慎,写完信还要检查个三四次,确保没有引人误会的内容才让送到相府去。
只能过书信往来,从不见面也是怕有人参他私下结交大臣,没想到这份小心谨慎反而成了杀他的利刃。
在皇帝看来,他是拒不认罪。
皇帝冷哼一声,“别以为你们藏得深朕就看不出来,什么藏头诗,什么暗号,朕统统都知道!”
秦君郁了然,看来是有人刻意曲解了他信中的意思。
而上位者,疑心病是最重的。
父皇本就有意借此试探他和年丞运的态度,被人这么一挑唆,都不用什么证据,直接就能给他定罪。
既然已认定他做了,那再怎么解释都显得是欲盖弥彰。
秦君郁没有说话,目光低垂。
年丞运心里头跟明镜儿似的,谁要害他,谁要害太子,在这局势中十分明朗,唯独皇帝,气昏了头,不明是非。
这样大逆不道的话他不敢说,干脆也闭嘴。
两人都沉默,皇帝只当他们对罪行供认不讳。
“来人!上廷仗!”皇帝冷声吩咐,目光只擒年丞运,“年丞运结党营私,教唆太子行不孝之事,理应重罚。”
“然,念其年事已高,多年来劳苦功高,故当众杖责三十,以儆效尤,望众爱卿引以为戒,莫要再生出这样的事来。”
一声令下,护麟卫的人立马抬了长凳上来,驾在殿中间,其中两名手上抱着七尺长的粟板,气势凌人。
不少官员被这阵仗吓得抖了三抖。
被处以廷杖的官员,历代以来并不少,但像年丞运这种位高权重的却少之又少,廷杖,是皇帝处罚犯错的大臣的手段之一,亦是最侮辱人的种。
试想一个高风亮节,峨冠博带的文人被当众打得皮开肉绽,鲜血淋漓,须得要人抬着才能行动,那他以后还有何种脸而谈文人风骨?
年丞运望着那冰冷冷的长凳,身子一歪,绝望地闭了闭眼。
秦君郁亦是不忍。
打人所用的粟板,击人的一端上装有倒勾,一板下去,又上来,行刑人一扯,尖利的倒勾就会把受刑人身上连皮带肉撕下来一大块,不出下下,受刑人的皮肉就会被撕得一片稀烂。
孤岛之王
...
画里长安
一朝穿越,她成了玉石商人的痴傻女儿,父亲无辜被杀,她只能寄人篱下,虽然身世凄苦,却难掩耀目的绘画天赋,原本只想安安稳稳地虚度余生,怎知半路遇到了他,格格不入的尘世邂逅,命运将她演变成一个遗世独立的旷代逸才,究竟是女扮男装的画师,还是傲立绝世的美人,也许只能从画卷中一探究竟...
郁笙慕景珩
...
三国从忽悠刘备开始
汉灵帝西园租官,要不要租?租!当然租!因为只要恰好租到灵帝驾崩前的最后一个任期,就等于直接租房租成了房东!租官租成了诸侯!所以,匡扶汉室怎么能只靠埋头苦战...
绯闻前妻:总裁离婚请签字
许绒晓从来不知道自己能够嫁给欧梓谦是幸还是不幸。她和他的脚步似乎永远都不在一个频率。她爱他时,他不爱她。她拼命讨好时,他厌倦她。终于,她累了,想抽身而退了,他却又缠上来,霸占着她。爱吗?可结婚三年,除了至亲,无一人知道许绒晓是欧梓谦的妻。不爱吗?可她疯了三年,他却不离不弃,每日以挨她一个耳光,换她吃一口饭的方式,把她养的健健康康。哭过,笑过,分过,闹过兜兜转转一圈,他们才终于意识到彼此在生命中存在的意义。欧梓谦是许绒晓的劫,许绒晓是欧梓谦的命!...
巅峰战神
世间有少年,从西向东,孤绝而热勇。曾家仇未报,曾默默无闻,却从不言退怯。四面萧索,八面埋伏,他以纵横之气横扫千军。山是山,河是河。苍穹大地,众生之巅。唯有巅峰战神!...